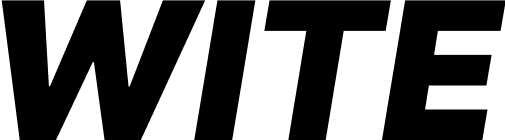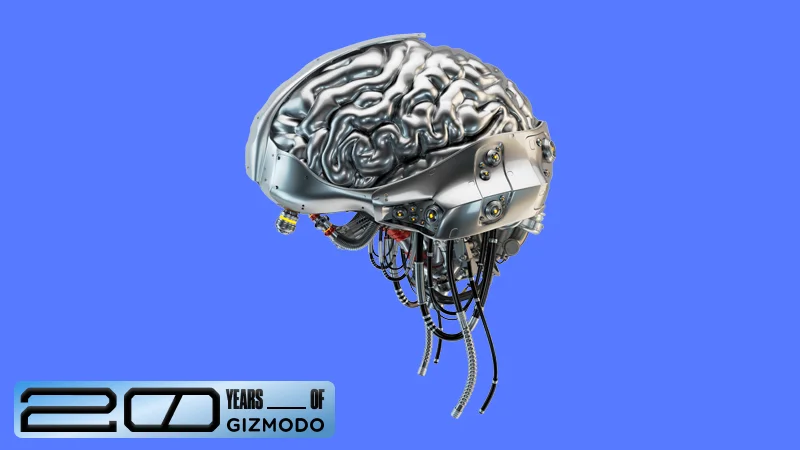像9/11过后的许多人一样,我感到精神存在上的迷失。现在很难相信,但我当时是一个经常去教堂的人。看着那些飞机撞向世贸中心,把我从长时间的大脑沉睡中唤醒,从那以后,除了偶尔的婚礼或洗礼,我再也没有踏进过教堂。
当时我并没有意识到,但那糟糕的一天引发了我个人的复兴,我对科学和哲学的热情被重新唤醒。我的婚姻没有在这次精神重启和恢复中幸存下来,但它确实把我带到了一些非常积极的地方,导致我采用了世俗佛教、冥想和长达十年的素食主义。它还将我引向了未来主义,特别是一种被称为超人类主义的未来主义。
超人类主义对我来说很有意义,因为它似乎代表了我们进化过程中合乎逻辑的下一步,尽管是由人类而非达尔文选择引导的进化。作为一种文化和知识运动,超人类主义试图通过开发、推广和传播能够显著提高我们的认知、身体和心理能力的技术来改善人类的状况。当我第一次偶然发现这个运动时,超人类主义的技术推动者开始成为焦点:基因组学、控制论、人工智能和纳米技术。这些工具有可能从根本上改变我们的物种,使人类拥有更多的智力和记忆,无限的寿命,以及全新的身体和认知能力。作为一个新生的佛教徒,超人类主义有可能通过消除疾病、医务室、精神障碍和衰老的摧残而减轻大量的痛苦,这对我来说意义重大。
人类将过渡到后人类状态的想法似乎既不可避免又很理想,但是,拥有一个明显的功能性大脑,我立即意识到潜在的巨大危害。为了避免《勇敢的新世界》的二元论(也许是虚荣心作祟),我决定直接参与到超人类主义运动中,希望能将其引向正确的方向。为此,我开设了自己的博客,Sentient Developments,加入了世界超人类主义协会,与他人共同创办了现已解散的多伦多超人类主义协会,并担任超人类主义电子杂志Betterhumans的副编辑,该杂志也已解散。我还参与了伦理与新兴技术研究所(IEET)的创建,并继续担任该研究所的董事会主席。
事实上,也正是在2000年代早期到中期的这个时候,我对生物伦理学产生了热情。这种新发现的魅力,加上我对未来主义研究和推广的兴趣,带来了许多令人眼花缭乱的机会。我在学术会议上发表演讲,定期出现在广播和电视上,参与公共辩论,并组织了以超人类主义为主题的会议,包括2004年的TransVision,其中有澳大利亚行为艺术家Stelarc、加拿大发明家和半机械人Steve Mann和抗衰老专家Aubrey de Grey的演讲。
超人类主义运动几乎渗透到了我生活的各个方面,我几乎没有想到别的。它还把我引入了一个有趣的(有时是有问题的)人物阵容,其中许多人仍然是我的同事和朋友。该运动在2000年代末和2010年代初聚集了稳定的势头,获得了许多新的支持者和健康的反对者。超人类主义备忘录,如思想上传、转基因婴儿、克隆人和激进的生命延长,与主流调情。至少在一段时间内如此。
几乎没有过气
超人类主义 “这个词是在20世纪突然出现的,但这个想法存在的时间比那要长得多。
对不朽的追求一直是我们历史的一部分,而且可能永远都是。美索不达米亚的《吉尔伽美什史诗》是最早的书面例子,而不老之泉–字面上的不老之泉–是西班牙探险家胡安-庞塞-德莱昂的痴迷。
人类可以以某种方式被改造或增强的概念出现在18世纪的欧洲启蒙运动中,法国哲学家丹尼斯-狄德罗(Denis Diderot)认为,人类有朝一日可能将自己重新设计成多种类型,”其未来和最终的有机结构是无法预测的”,正如他在《达朗贝尔的梦》中写道。狄德罗还认为有可能让死人复活,给动物和机器注入智慧。另一位法国哲学家孔多塞侯爵(Marquis de Condorcet)也有类似的想法,考虑到乌托邦社会、人类的完美性和生命的延长。
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的俄罗斯宇宙主义者预示了现代超人类主义,因为他们思考了太空旅行、身体恢复活力、不朽和起死回生的可能性,后者是冷冻学的预兆–现代超人类主义思想的主要内容。从20世纪20年代到50年代,英国生物学家霍尔丹(J. B. S. Haldane)、爱尔兰科学家贝纳尔(J. D. Bernal)和英国生物学家朱利安-赫胥黎(他在1957年的一篇文章中推广了 “超人类主义 “一词)等思想家都公开倡导人造子宫、克隆人、控制论植入、生物增强和太空探索等事物。
超人类主义者,起来吧!
然而,直到20世纪90年代,才出现了一个有凝聚力的超人类运动,这一发展主要是由互联网带来的。
“与许多小型亚文化一样,互联网让世界各地的超人类主义者开始在电子邮件列表上交流,然后是网站和博客,”生物伦理学家、社会学家和IEET的执行董事詹姆斯-休斯告诉我。”几乎所有的超人类主义文化都在网上进行。20世纪90年代和21世纪初也相对繁荣,至少对超人类主义发展的西方国家来说是这样,所以超人类主义的技术乐观主义似乎更有说服力”。
互联网无疑催生了充满活力的超人类主义亚文化,但诱人的、有影响的科技概念的出现才是该运动的实质。多莉羊,世界上第一只克隆动物,于1996年出生,次年加里-卡斯帕罗夫成为第一个输给超级计算机的国际象棋大师。人类基因组计划终于在2003年发布了完整的人类基因组序列,这个项目花了13年才完成。互联网本身催生了许多未来主义的概念,包括在线虚拟世界和将个人意识上传到计算机中的前景提出了一个可能的底层–法国耶稣会哲学家泰尔哈德-夏尔丹设想的一种全球思想。
关键的拉拉队为遥远的未来主义思想的扩散做出了贡献。埃里克-德雷克斯勒的开创性著作《创造的引擎》(1986年)展示了分子纳米技术惊人的潜力(和危险),而汉斯-莫拉维克和凯文-沃里克的工作也分别对机器人和控制论做了同样的描述。未来学家雷-库兹韦尔(Ray Kurzweil)通过他的 “加速回报法则 “和对摩尔定律的迷信,使许多人相信一个激进的未来就在眼前;在他的流行书《精神机器时代》(1999)和《奇点临近》(2005)中,库兹韦尔预言人类智慧正处于与技术融合的边缘。在他看来,这意味着我们可以期待在21世纪中期出现技术奇点(出现比人类更强大的人工智能)(作为一个想法,奇点–另一个超人类主义的主食–自20世纪60年代就已经存在,并在未来学家和科幻作家Vernor Vinge 1993年的一篇文章中被正式确定)。2006年,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资助的一份报告,题为 “管理纳米-生物-信息-认知创新。社会中的融合技术”,表明美国政府开始关注超人类主义思想。
一个充满活力的基层超人类主义运动在千年之交发展起来。由未来学家马克斯-莫尔(Max More)创立的Extropy研究所和世界超人类协会(WTA),以及其国际特许团体,为过去和现在的一系列疯狂分歧的想法提供了结构。一些具有相关兴趣的专业团体也出现了,包括:玛土撒拉基金会、奇点人工智能研究所(现在的机器智能研究所)、负责任的纳米技术中心、展望研究所、救生艇基金会,以及其他许多团体。人们对冷冻学的兴趣也在增加,阿尔科生命延续基金会和冷冻学研究所受到了比以往更多的关注。
社会和文化匆匆变得赛博朋克化,这自然导致人们对未来的思考越来越多。随着阿波罗时代在后视镜中消失,公众对太空探索的兴趣减弱了。厌倦了以太空为中心的《2001:太空漫游》和《星球大战》,我们越来越多地将注意力转向有关人工智能、控制论和超级计算机的电影,包括《银翼杀手》、《阿基拉》和《黑客帝国》,其中许多电影都带有独特的反乌托邦色彩。
随着超人类主义运动的全面展开,愤怒的嚎叫声变得更加响亮–从保守的宗教右派到反技术左派的批评者。政治学家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宣布超人类主义是世界上最危险的思想是超人类主义的强烈批评者,他领导了小布什总统的生物伦理委员会,该委员会明确处理旨在提高人类能力和外观的医疗干预措施)。21世纪的生物伦理学战线,似乎正在我们眼前划定。
那是一个超人类主义的黄金时代。在一个看似不可能的短时间内,我们的想法从默默无闻变成了搔扰时代潮流。对我来说,真正成功的时刻是看到《时代》周刊2011年2月21日的封面,标题是 “2045年:人类成为不朽的那一年”,封面艺术描绘了一个大脑被劫持的人头。
到了2012年,我自己在这方面的努力为我找到了一份工作,成为io9的特约编辑,这有助于进一步扩大我对科学、未来主义和哲学的兴趣。我在2014年的Moogfest上发表了演讲,并有一些未来主义的副业,担任了国家地理杂志2017年的纪录片-剧集《百万年》的顾问。那时,无论是在io9还是后来在Gizmodo,超人类主义的主题渗透了我的许多工作,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情况越来越少。这些天来,我几乎没有写过关于超人类主义的文章,我对这一运动的参与也几乎没有被提及。我的重点是太空飞行和正在进行的太空商业化,这继续满足我的未来主义之痒。
“我们正生活在一个部分超人类的世界中”
曾经的刺耳吼声已经退缩到几乎无法辨别的背景噪音。或者至少在我看来,这就是目前的情况。由于明显和不明显的原因,关于 “超人类主义 “和 “超人类主义者 “的明确讨论已经被搁置一旁。
正如牛津大学人类未来研究所的高级研究员安德斯-桑德伯格(Anders Sandberg)告诉我的那样,我们不再像以前那样谈论超人类主义的原因是,它的大部分内容已经变得有点正常—至少就技术而言。
“我们使用可穿戴设备(智能手机)在线生活,在人工智能和智能增强的帮助下,虚拟现实又回来了,基因治疗和RNA疫苗是一个东西,大规模的卫星星座正在发生,无人机在战争中变得很重要,跨[性别]权利是一个大问题,等等,”他说,并补充说。”我们正生活在一个部分超人类的世界中。然而,与此同时,”刻意拥抱变化并试图以这样的未来为目标 “的超人类主义思想还没有成为主流,”桑德伯格说。
他关于超人类主义与跨性别权利有关的观点可能会让人感到惊讶,但未来主义者与LGBTQ+问题的联系可以追溯到很久以前,无论是科幻小说家奥克塔维亚-巴特勒设想的同性恋家庭和更大的性别流动性,还是女权主义者唐娜-哈拉维渴望成为一个机械人而不是一个女神。超人类主义者长期以来一直倡导扩大性和性别的多样性,以及相关的身体自主权和调用这种自主权的手段。2011年,亿万富翁超人类主义者和变性人权利倡导者Martine Rothblatt更进一步,她说:”我们不能对超人类主义产生于变性人的蹊径感到惊讶,””我们必须欢迎这种对任意生物学的进一步超越”。
Natasha Vita-More是Humanity+的执行董事,自20世纪80年代初以来一直是活跃的超人类主义者,她说20年前对非超人类主义者来说是陌生的想法已经融入我们的常规词汇中。她说,这些天来,具有超人类主义思想的思想家经常提到冷冻技术、思想上传和记忆转移等概念,但不必援引超人类主义。
我们不再像以前那样引用超人类主义是好事吗?”维塔-莫尔告诉我:”不,我不这么认为,但我也认为这是社会理解的成长和演变的一部分,因为我们不需要关注哲学或运动,而不是改变世界的技术或科学进步。此外,”今天的人们对技术的了解远远超过20年前,他们更善于考虑变化的利弊,而不仅仅是弊端或潜在的坏影响,”她补充说。
未来学家顾问、以超人类为主题的科幻小说《凤凰地平线》三部曲的作者PJ Manney说,所有对未来人类的积极和乐观的愿景 “正在被削弱或彻底破灭,因为我们看到人类使用新的工具,做人类做的事:好的、坏的和丑的。”
的确,与20年前相比,我们对技术更加愤世嫉俗和警惕,而且有充分的理由。剑桥分析公司的数据丑闻、爱德华-斯诺登对政府间谍活动的揭露以及种族主义警务软件的出现,都是一批令人震惊的可谴责的发展,表明技术有可能变坏。
与我一起在IEET董事会任职的曼尼继续说,我们不再那么多地谈论超人类主义,”因为它的很多东西已经在文化中了”,但我们 “存在于深刻的未来冲击中”,”文化和社会压力就在我们周围”。曼尼提到了 “倒退的上合组织委员会的逆转”,以及美国各州如何从公认的人类身上取消人权。她建议我们在 “考虑我们的硅模拟物 “之前为人类确保人权。
奈杰尔-卡梅伦(Nigel Cameron)是超人类主义的直言不讳的批评者,他说未来主义运动失去了很多吸引力,因为随着隐私、自动化和基因操作(如CRISPR)等独特的挑战开始出现,天真的 “讨论中的巨大变化和进步的框架 “变得不再有趣。在21世纪初,卡梅伦在伊利诺伊理工学院领导了一个关于新兴技术的伦理学项目,现在是渥太华大学科学、社会和政策研究所的高级研究员。
长期从事超人类主义的组织者和学者桑德伯格说,2000年代的反恐战争和其他新出现的冲突导致人们转向 “现在的地缘政治”,而气候变化、中国的崛起和2008年的金融危机导致了2010年代所看到的悲观主义。桑德伯格说:”今天我们遇到了严重的问题,愤世嫉俗和悲观主义麻痹了人们试图修复和建设事物的努力,”。”我们需要乐观主义!”
持久印象
一些在20世纪90年代和2000年出现的超人类主义团体仍然存在,或演变为新的形式,虽然仍有一个强大的支持超人类主义的亚文化,但更多的公众似乎脱离了,基本上不感兴趣。但这并不是说这些团体,或一般的超人类主义运动没有影响。
各种超人类主义运动 “导致了许多有趣的对话,包括一些将保守派和进步派聚集在一起的共同批评,”卡梅伦说。
“桑德伯格说:”我认为这些运动主要是作为知识分子的沙龙产生了影响,在那里,蓝天白云的讨论使人们发现了重要的问题,他们后来在专业上进行了挖掘。他指出牛津大学的哲学家和超人类主义者尼克-博斯特罗姆,他 “发现了存在风险对思考长期未来的重要性”,这导致了一个全新的研究方向。剑桥大学的存在风险研究中心和牛津大学的人类未来研究所(https://www.fhi.ox.ac.uk/)是博斯特罗姆工作的直接成果。桑德伯格还引用了人工智能理论家埃利泽-尤德考夫斯基,他 “完善了对人工智能的思考,导致了人工智能安全社区的形成”,还有超人类主义的 “加密无政府主义者”,他们 “为加密货币世界做了基础工作”,他补充说。事实上,以太坊的联合创始人维塔利克-布特林赞同超人类主义思想,他的父亲德米特里曾经参加我们在多伦多超人类主义协会的会议。
根据曼尼的说法,各种由超人类主义驱动的努力 “激发了包括我自己在内的许多人的词汇和创作冲动,以争夺自然产生的哲学、技术和艺术影响”。科幻作品与超人类主义的斗争 “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激烈,无论人们是否意识到这一点,”她说。有道理。像《人类》、《黑色孤儿》、《西部世界》、《黑镜》和《Upload》这样的节目都充斥着超人类主义的主题和问题,尽管这个词本身很少—如果有的话—被说出来。也就是说,这些节目大多是反乌托邦性质的,这表明超人类主义大多是通过灰色的眼镜来看的。公平地说,对未来的超级振奋人心的描绘很少能成为好莱坞大片或热门电视节目,但值得指出的是,《圣朱尼佩罗》因其对上传作为逃避死亡的手段的积极描绘而被评为《黑镜》的最佳剧集之一。
然而,在大多数情况下,超人类风味的技术是可以理解的可怕的,而且相对容易被投以负面的眼光。不加批判和满怀希望的超人类主义者,其中有很多,并没有什么帮助。曼尼认为,超人类主义本身可以使用升级。”她告诉我:”缺乏对后果和后续影响的考虑,以及超人类主义常见的自恋要求,一直是该运动的败笔。”小心你所希望的,你可能会得到它。” 曼尼说,无人机战争、监控社会、深层假象,以及可黑客化的生物假肢和脑芯片的潜力,使超人类主义的想法变得不那么有趣。
像许多其他边缘社会运动一样,超人类主义 “通过扩大关于人类增强的政策和学术辩论中的’奥弗顿窗口'[也被称为话语窗口],产生了间接影响。”休斯解释说。”在2020年代,超人类主义仍然有它的批评者,但它被更好地认可为一种合法的知识立场,为更温和的生物自由主义者提供一些掩护,以争论自由化的增强政策。”

桑德伯格提出了一个非常好的观点:”没有什么比未来的愿景更快变老”。的确,20世纪90年代的许多超人类主义想法现在看起来已经过时了,他指着可穿戴电脑、智能饮料、即将到来的寿命延长,以及 “所有那些互联网乌托邦主义”。尽管如此,桑德伯格认为超人类主义的基本愿景仍然完好无损,他说 “人类的状况可以被质疑和改变,而且我们在这方面越来越好”。这些天,我们谈论CRISPR(一种2012年出现的基因编辑工具)比谈论纳米技术更多,但超人类主义 “随着新的可能性和论点的出现,自然会升级自己”,他说。
维塔-莫尔说,超人类主义的愿景 “仍然是可取的,而且可能更加可取,因为它对许多人来说已经开始有意义了”。增强的人类 “无处不在”,她说,从 “植入物、我们日常使用的智能设备、人类与我们日常使用的计算系统的整合,到希望有一天我们能够减缓记忆的丧失,并在记忆丧失或痴呆症和阿尔茨海默病的情况下存储或备份我们的神经功能。”
关于超人类主义 “对许多人来说已经开始有意义 “的看法是很好的。以Neuralink为例。SpaceX首席执行官埃隆-马斯克(Elon Musk)将这家初创公司建立在两个非常超人文主义的原则之上–大脑和计算机之间的接口是可能的,人工超级智能即将到来。马斯克,以其典型的方式,声称想要建立神经接口设备的动机是慈善的,因为他认为增强的大脑将保护我们免受恶意机器智能的影响(我个人认为他错了,但这是另一个故事)。
对卡梅伦来说,超人类主义看起来和以前一样可怕,他磨练了一个概念,他称之为 “人类的空洞化”,即 “智人的所有重要的东西都可以被上传,作为我们欲望的范本 “的想法。在过去,卡梅伦认为,”如果机器智能是人类卓越的典范,并得到提升和接管,那么我们将面临一个新的封建主义,因为对金融和与之相关的权力的控制将是人类技术提升的核心,而民主……将在水中死亡。”
超人类主义与未来主义的未来
也就是说,尽管有这些担忧,曼尼认为仍然需要一个超人类主义运动,但 “一个为全人类解决复杂性和变化的运动”。
同样,维塔-莫尔说,仍然需要一个超人类主义运动,因为它的作用是促进变革,支持基于 “个人需求 “的选择,着眼于 “超越二元思维”,同时也支持 “多样化的善”。
“总是需要智囊团的存在。虽然有许多未来学家团体在思考未来,但他们主要集中在能源、绿色能源、风险和道德方面,”维塔-莫尔说。”除了后现代主义的立场,这些团体中很少有关于人类未来的知识或信息的可靠来源,后现代主义的立场更注重女权研究、多样性和文化问题。” 维塔-莫尔目前担任Humanity+的执行董事。
休斯说,当超人类主义者试图定义他们真正想要的东西时,他们陷入了一些政治、技术、甚至宗教阵营。IEET将其超人类主义的品牌描述为技术进步主义—正如休斯所定义的那样,”试图定义和促进一个增强的未来的社会民主愿景”。休斯说,作为一个概念,技术进步主义比超人类主义提供了一个更具体的组织基础,所以 “我认为我们已经远远超出了’超人类主义’运动的可能性,现在将看到一系列受超人类主义启发或影响的运动的增长,这些运动具有更具体的身份,包括摩门教徒和其他宗教的超人类主义者,自由主义者和技术进步者,以及正在进行的长寿主义、人工智能和脑机亚文化。”
“我确实认为我们需要公共知识分子更认真地把这些点联系起来,因为技术继续融合,为人类的状况提供了祸害和祝福,而我们的反应往往是不加批判地热情,或者也许是不热情,”卡梅伦说。
桑德伯格说,需要超人类主义作为 “我们文化中普遍存在的悲观主义和愤世嫉俗的对立面”,而且要 “想要拯救未来,你需要既认为它将足够棒,值得拯救,又认为我们有能力做一些建设性的事情。” 对此,他补充说:”超人类主义也增加了多样性—未来不一定要像现在这样。“
正如曼尼恰当地指出的那样,在美国的堕胎权被取消的时候,鼓吹人类的增强似乎很可笑。在covid-19疫情期间,反打疫苗者的崛起带来了另一个复杂的问题,显示了公众愿意拒绝一件好事的程度。对我个人来说,反疫苗主义者对这一流行病的反应特别令人沮丧,因为我经常引用疫苗来解释超人类主义的心态—我们已经接受了加强我们有限的遗传禀赋的干预措施。
鉴于目前的情况,我自己认为,自称是超人类主义者的人应该倡导和鼓动完全的身体、认知和生殖自主权,同时也要倡导科学论述的优点。在这些权利确立之前,赞美改善记忆或从根本上延长寿命的好处似乎有点为时过早,尽管不得不承认这一点很令人难过。
撇开这些当代社会问题,超人类的未来不会等待我们去追赶。这些技术将会到来,无论它们是出现在大学实验室还是企业车间。其中许多干预措施将对人类大有裨益,但其他干预措施可能导致我们走上一些严重的黑暗道路。因此,我们必须将对话向前推进。
这让我想起了我当初参与超人类主义的原因—我希望看到这些变革性技术的安全、理智和可及的实施。无论是否明确提到超人类主义,这些目标仍然是值得的。值得庆幸的是,这些对话正在发生,我们可以感谢超人类主义者作为煽动者,无论你是否赞同我们的想法。